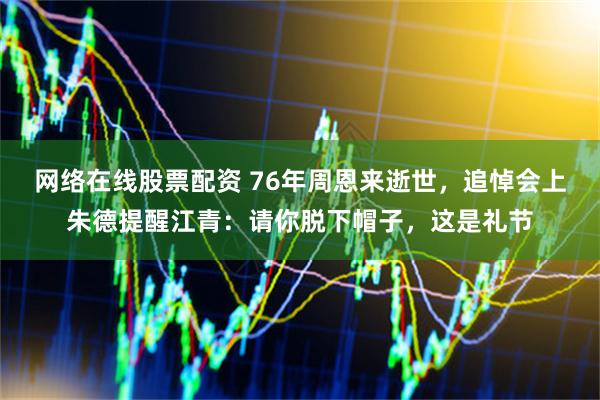
1976年1月15日凌晨五点,北京殡仪馆外的北风像刀子。守灵的卫士赵一鸣揉着通红的手,抬头望见远处一排黑色轿车正缓缓驶来。今天网络在线股票配资,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就要举行,城里的交通灯全调成了绿色,所有人都知道:总理最后一次“出行”,不能被任何红灯拦住。
车门打开,治丧委员会成员鱼贯而下。朱德戴着黑臂章,步子虽然慢,却依旧挺直;邓颖超裹着一件深灰色大衣,眼睛红肿得厉害。灵堂里布置早已完成,正中的遗像取自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那天,总理笑得很淡,却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。
灵柩四周摆满白菊。按照周恩来的遗愿,骨灰最终要洒向大海,但在此之前,他仍要向党旗作最后的告别。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名誉主任,共107人。名单贴在门口,密密麻麻,全是老战友:朱德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李先念……名字与共和国历史一一对应。
上午十时整,礼宾司确认外事宾客已全部就位,告别仪式正式开始。朱德走到灵柩旁,右手颤抖,却仍举到眉间,敬了一个标准军礼。随后,他退到侧面,给江青让出位置。
就在这时,一个小小的插曲发生了。江青戴着一顶深色毡帽,低头向前。殡仪礼宾官轻声提醒:“江青同志,请您脱帽。”江青没有动作,嘴里轻声说出两个字:“感冒。”声音不高,却被朱德听见。朱德眉头一皱,侧身半步,声音低沉却清晰:“请你脱下帽子,这是礼节。”一句话,不疾不徐。江青愣住几秒,最终取下帽子。短暂的僵硬,没能盖过哀乐声。
哀乐响起,邓小平站在麦克风前宣读悼词。读到“心脏停止跳动”时,他咬了咬嘴唇,声音一下子低了半度。很多人第一次发现,那个以“钢铁”著称的副总理也会在公众场合红了眼眶。
人群肃立,许多人回想起八天前的清晨。1月8日9时57分,解放军301医院心电图上的一条直线宣告——周恩来走了。医生张佐良按下抢救铃,十五分钟的胸外按压没有奇迹。邓颖超赶到病房时,守在门口的护士已泣不成声。周恩来的遗体被转送北京医院太平间,理发师朱殿华负责整理仪容,老工匠剪完最后一缕头发时,两行热泪掉在白色床单上。
许多人说,总理其实早在1972年就该好好休息。那年二月尼克松访华,一周行程,周恩来几乎全程陪同。两个月后,尿检出现异常;1974年2月确诊为膀胱癌,三次电灼,两次手术,身体仍在苛求自己。1975年11月后,他连坐起都困难,却仍批阅文件。护士夜里给他喂药,他轻声叮嘱:“别惊动警卫,大家都很累。”短短十字,连呻吟都压低。
1月7日,病房灯光昏黄,周恩来忽然睁眼,对轮班医生说:“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吧,这里没事。”这成了最后一句话。听者无不低头抹泪,却又不敢抽泣出声,怕惊扰病榻上那位老人。
追悼会进入告别环节,队伍绵延到院外。有人算过,一个小时过去,行礼的队伍还没缩短。北京1月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,但没有人抱怨。灵堂外墙上悬挂的黑底白字挽联,在风中猎猎作响,像在提醒:这位倾尽一生心力的老人终于可以休息了。
当天傍晚,工作人员遵照毛泽东批示,将骨灰装入四只文件袋。17日清晨,专机从通县机场起飞,第一次盘旋后机舱门打开。邓颖超抱着文件袋,身体前倾,灰白色的粉末瞬间融入云层。随后,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口、黄河入海口三次投撒。罗盘指针无声旋转,机舱内一片肃穆。

骨灰撒完返回首都,文件袋已空,只剩少量灰粉粘在封口。工作人员遵照遗嘱,将空袋放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,桌上摆了六盆水仙。夜深灯暗,警卫换岗时偶尔回头,看到淡黄色花蕊在绿叶间微微颤动,像极了总理生前那抹节制却温和的笑。
有人翻检周恩来的遗物,旧衣服补丁密布,只有一块手表还能走时。叶剑英看完登记表,沉默许久:“他给党和国家留下了巨大的财富,却没给自己留下半件好东西。”随后合上文件,抬手敬礼。
1976年终,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离世,年轮翻过半个世纪。那些在历史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,其实都曾像普通人一样在病痛里挣扎,在礼节里争执,在困难里咬牙。追悼会上的那声“请你脱下帽子”,不仅是对仪式的坚守,也是老一辈革命者骨子里最朴素的原则——尊重。
博星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